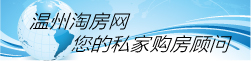城市规划、住房建设,塑造的是一种凝固的社会架构。如果这种凝固的架构是以贫富分化为前提,那么就可能把已有的贫富差别固定下来。这对一个社会而言,是莫大的威胁。
任志强先生最近说了“可恨的真话”:开发商就应该为富人服务,穷人富人分区天然合理,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。一时间网络、媒体为之沸腾。
任先生的话确实有不少“真”的成分。可惜他有两个问题。第一:他只讲了一半真话,另一半藏着。第二,他似乎把现实的都看成是合理的,话里话外,贫富分区成了一种理想,而不是病症。
先说他那一半真话。不错,只要富人钱来得正当,当然有权在市场上买自己喜欢的住房、住好一点的区。其实,老百姓对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异议。以我的孤陋寡闻,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,穷人区富人区一直是有的,但成为媒体热点,如今似乎还是第一次。这说明大家过去对这种现象还是基本接受了的。为什么现在开始辩论这个问题?关键不在于富人愿意住自己的区,而是有些富人抢了穷人的地方。任先生没有提的另一半真话是,许多开发商的财富,是建在拆迁基础上的。许多富人区,是在把穷人赶走而没有进行应有补偿的情况下建造的。这才是民愤汹汹的一大原因。
二十年前,我住的地方有许多民房,老百姓临街开店,生意火得很。可后来有人觉得破旧的民房碍眼,就盖了一堵墙,把民房封在里面。墙外侧粉刷成红色,上面还加了琉璃瓦,颇为可观。但内侧连基本的粉刷也没有,老百姓原来临街的门窗,对着一面劣质砖头,一点儿阳光也没有,可谓“未敢出门已碰头”。更糟的是,这一堵墙,把一条街的个体户生意都给封了。后来干脆连墙带民房一并拆掉。许多人家在那里住了半个世纪以上,说走就得走。
你可以说穷人应该希望富人都住上好房,这样缴税多,国家用来补贴穷人住房的资金也多。但是,穷人也不是要饭的命,只配等人家施舍。当年地坛一带的居民,个体户甚多,许多人仗着他们居住的风水宝地,不少赚钱。等几年人家也成了富人了。而现在,由于一些不合法的拆迁,把穷人都挤走,把人家致富的机会给砸了,腾出地方给富人盖房,然后再说穷人惟一的指望是等富人都住上好房、缴了税后,国家可以给他们一些救济。这是否有些太傲慢呢?
老百姓恨的不是富人,他们恨的是掠夺致富。房地产开发商,很多人欠着这些被赶走的穷人的债。我并非反对市场竞争。相反,我主张在保障竞争者权利的前提下的充分市场竞争。用违法拆迁赶走老百姓,这是合理的市场竞争吗?
再有,贫富分区虽然各国都有,而且永远无法根除,但发达国家大都把这种分区看成社会问题。任先生忽视了这一点。比如他讲到洛杉矶贫富区之判然可分,字里行间,透露出赞赏之意,仿佛这就是天理。他似乎忘记了,十几年前洛杉矶大骚乱时,美国媒体连篇累牍报道当地的社会问题,其中之一就是这种贫富分区。去年年底法国骚乱,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因为贫富分区。在社会管理成熟的国家,很少有人天真到认为这样的问题可以得到根本救治,但也很少有人玩世不恭到认为全社会不值得努力缓解这样的问题。
任先生作为一个开发商应该明白,城市规划、住房建设,塑造的是一种凝固的社会架构。如果这种凝固的架构是以贫富分化为前提,那么就可能把已有的贫富差别固定下来。这对一个社会而言,是莫大的威胁。所以,房地产开发商必须承担社会责任。如果他们拒绝承担,社会就要强迫他们承担。比如我居住的大波士顿地区,几乎每个镇都有义务在新建的住房中建一定比例的经济适用房。更有专家讨论如何建设贫富混居的住房体系,在凝固的架构中创造社会流动的“动感”。
我的隔壁邻居,就是一位靠给人家看孩子度日的穷人,几乎很难支持自己的生活。但另一个邻居则是位富人,女儿几乎一天公立学校都没有上过,一路私立贵族学校上下来,今年哈佛毕业。有一次听《纽约时报》一位女黑人专栏作家讲,她刚搬进一栋公寓楼,第二天一位白人家庭主妇就来敲门,问她能否给他们家看孩子。这位作家的主旨是说,因为她是黑人,白人天然就认为她是个保姆,想不到她也属于纽约的上流社会。不过,她无意透露出来,这栋公寓《纽约时报》的专栏作家住,大概保姆们也有住过的。否则,她也不会一搬进来就被盯上。
如果常常把大片老百姓的居住区拆迁,然后建豪华住宅和豪华办公楼、购物中心,不仅不限制贫富区的分化,而且人为助长这种分化,老百姓当然要愤怒。这才是问题的根本。我们现在要做的,是如何通过住房建设连接而非分化不同的阶层。社会对房地产开发商应该提出更高的要求。比如,所建的20%的住房,必须以低价向低收入家庭出售,而且地点就要在“富人区”内;当不得不拆迁时,必须就地给被拆迁户盖新房。如果这样的规则对所有人一视同仁,照样有市场竞争。聪明的开发商会想出解决不同阶层人需要的办法。这样当然提高了开发商的成本,不过这种成本最终会部分转移到富人头上,让他们买房贵一点而已。而如今赶走穷人盖富人区的作法,实际上是让穷人补贴富人。这不叫市场经济。
作者系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薛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