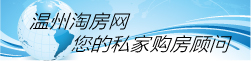“这里住的最多的还是大学毕业生。”因为住地下室需要登记身份证,王名发现租客身份证很多都印着大学的集体宿舍。
王雷就是其一。2010年,从南京某大学广告专业毕业的王雷漂到北京。最初,王雷在南三环附近租了一间公寓。但每月700多的房租让他无法承担,当时正在实习的他每月薪水才1千多快钱,“房租就占了大半,生活几度出现窘境,而且北京的房租也在涨。”为了克服这些困难,转入地下是王雷当时唯一的选择,他的房租也立即缩减到薪水的三分之一,“刚搬进地下室的时候我还是挺兴奋,至少摆脱了工作了仍然需要家里的贴补的尴尬状态。”
不过,王雷很快发现这间格子大的地下室存在种种问题:放在房间里的烟抽起来异常吃力、桌子上的书角都开始打卷、被子开始变得潮湿、电脑屏幕都有了水气……“太重的潮气让晚上的睡眠质量降低,因为身体总是感觉有些黏,常常感觉到腰疼。夜晚时分能很清晰地听闻到隔壁的种种声音。”
王雷打算工资涨到3000元时就离开,但是,他不知何时会涨工资,也不知那时能否还找到700元的房间。
和王雷同一年毕业的李峰也在这个地下室住。一间6平米的小房间,摆着一张床,一张桌子,剩下已没有多少空间。大部分时间,李峰或坐或躺在床上,电脑是他与外界联系的唯一纽带,“虽然几个房间共用一根网线,有时网速慢,但至少能上QQ。”
李峰说最难受的是早晨,每天早上,当李峰从沉睡中醒来时,在周围一片漆黑中,地下室的灯光会显得格外刺眼,到了地面,外面的阳光会让他再一次造成短暂的视觉障碍,“没有什么过度,与外界的反差太大了,眼睛有时睁不开。”
“我当然希望住到地上,但现在无力承担这么贵的房租。”李峰说。他其实很讨厌每天从地上回到地下,现在他会选择在附近的肯德基看书。不过,当这些店要关门时,他还是要回到地下,至少这里是他的休憩之所。李峰决定住完这个月就离开地下室,因为工作开始稳定,月收入能够达到4000多元。
“打持久战”的坚守者不过,也有的人选择在地下室“打持久战”。山东聊城的谢建良在地下室已经住了快两年,目前他并没有逃离的想法。
2009年7月,山东农业大学毕业的谢建良揣着1千多元钱来闯北京。在金台里的地下室,谢建良租了一个三人间的地下室,每个床铺290元,在精打细算中开始了他的工作历程。
谢建良的第一份工作是行业网站的编辑,这与他的专业工商管理有些搭不上边。“可能心态不好,我干完一个月就辞职了。”
谢建良的第二份工作是图书编辑,主要工作内容是校稿,出版社承诺一个月校80万字给谢建良4千元。谢建良希望能够借此搬离地下室。“但没想到,出版社许诺的兑现的差距太大,一个正式员工能拿到3千就算不错的,见习人员有时拿到手的只有1千多块钱,工资水平很低。”
谢建良又一次辞职,搬离地下室的想法也因此落空,此后他又不断地面试、换工作,但唯一没有换的就是这个地下室。
去年10月,谢建良应聘到一家广告公司当项目策划,月平均工资达到4000元以上。
可生活渐渐宽裕的谢建良,此时却放弃了搬离地下室的想法,“地下室挺好,冬暖夏凉,我去过朋友住的高楼,很热,又用不起空调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