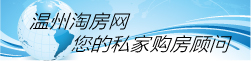很长时间里,我的居住理想就是拥有自己的一间筒子楼。
老朱的宿舍在西南楼,终于不用提心吊胆地通过学生宿舍的森严的门禁,我松了一口气。这个屋里住着四位大学教师,现在想来觉得不太对劲,但当时只是羡慕,住惯了八人间的我感觉到了天堂。
我那时的工作是给报社撰稿,有时甚至一天要写一万字,宿舍里的桌子几乎成了我专用的。每当写到主人公艰苦创业的情境,我就写得特别投入,特别动情,以至主人公自己读的时候也往往会感动得落泪。
其实,筒子楼时期,我感受到的更多是平和的温情。一到开饭时间,厌倦了食堂饭菜的居民们开始丁丁当当做饭,摆满了锅灶的走廊里,顿时香飘四溢。我所在的宿舍没有正经炉灶,从家带来的电火锅成了主要的炊具,大家开始是用来煮方便面,后来干脆把各种菜往里扔。可怕的是那锅里的汤经常几天不换,一位中央美院出身的室友还美其名曰“老汤”。
下雪的日子,几个人就着老汤里的新菜,喝常温的燕京啤酒,谈论着各种不切实际的理想,消磨一个晚上,是那一年最快乐的事。
地下室手记
看了托斯陀耶夫斯基的《地下室手记》和卡夫卡的《地洞》后,我有一度觉得地下室是一种适合自己的居住形式。在我想象中,地下室是一个安全、安静、冬暖夏凉,适合写作和思考的地方。
露宿事件之后,我在学校附今日焦点:
•揭开香港“迪斯尼酒店”内部装潢神秘面纱(组图) (图文) •陈淮:蓝筹房地产企业责任重大开发商不要太得意 •观望期上海开发商“心虚”北京开发商“嘴还硬”
近的地下室旅馆住过一夜,算是初尝了地下室的滋味。说实在的有点失望,四个上下铺,住着八个从来处来,将到去处去的陌路人,感觉远不如同样拥挤的学生宿舍。